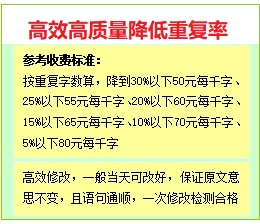所谓外在制约是指为实现秩序、福利及公序良俗而对基本权利所必需设定的且为宪法价值目标所容许的制约。此处的“秩序、福利及公序良俗”可统称为“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原则是现代宪法权利配置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根据该原则,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运动中,公共利益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支配地位,个人利益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居于受支配地位;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在同一领域相遇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于公共利益。早在倡导个人自由的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就已阐明了这一思想。如:格老秀斯认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比财产的主人更有权支配私人财产;孟德斯鸠也指出,共和政体“要求人们不断的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当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后,承认公共利益支配个人利益的人越来越多。
2. 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条款的立法表现方式
我国现行宪法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表现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概括式的立法方式
以概括限制的方式来规定公民基本权利问题,外国宪法多有此例。比如日本宪法第13条规定:一切国民都作为个人受到尊重。对于国民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祉,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予以最大尊重。我国宪法也采用了这样的立法体例,并在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里有几点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首先,新中国成立后曾颁布了四部宪法和一部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但只有现行宪法(即82年宪法)做了如此规定,这表明当时的修宪者为了宪法的科学性,力图借鉴外国立宪的合理模式;其次,修宪者结合中国的国情,表达了一种集体主义优位的诉求,因此“公共福祉”的语词在我国宪法的文本中置换成了“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再次,概括保留的立法方式,意在表征宪法对所有公民基本权利的一视同仁之保护,但却可能忽略了具体公民基本权利的本质或形式差异。
(2)区分式的立法方式
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之规定除了集中体现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以外,另外在第一章总纲的若干条款中也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宪法依据不同目的和各种具体基本权利的不同性质,做了区分式的限制规定,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
第一,专门性法律限制。这里的法律有特定的指涉,仅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通过的规范性文件。采行法律专门限制的方式,有多个条款。比如宪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第44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企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
第二,附条件的法律限制。此种限制方式在肯定国家公权力机关有权依照法律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同时,为了不妨碍公民基本权利的享有和行使,避免公民基本权利的空洞化,因此,对该权利限制的可能性和条件做了更加明晰化的预设。比如,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除外。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到底那些权利宜采取此种限制方式、如何合理地预设限制条件、限制的范围与程度是什么?这些都是我国今后修宪时应当特别重视的问题。
第三,一般性法律限制。按照现行宪法第33条3 款之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因此,我国任何公民都可在坚持该项原则的前提下,发展自己的自由空间,健全自己的人格质素,以期形成一个良好的宪政秩序。本条相对于宪法第51条而言,它要附属于后者所表达之限制目的,同时从实践操作层面来说,当不同宪法条款所确认之公民基本权利因价值位阶不清晰而发生冲突时,其取舍就必须以宪法第51条所表达之价值理念为据。有鉴于此,宪法第33条3款之规定,仅构成宪法51条之补充,它只是区分式立法方式的一种,似不宜被单独看作一个概括式的限制条款。
第四,隐含性(空白性)法律限制。其专指宪法有关公民具体基本权利的条款规定中,没有任何关于此项权利的限制规定,但这并不意味它的享有和行使是超限制的和无限制的。因为权利和自由以法律存在为前提,那里没有法律,那里便没有权利和自由,故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宪法和法律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权利的一种限制。任何权利包括以本立法例表现的权利,都不得不受宪法所表达和追求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秩序的限制。法国连带主义法学家狄骥认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世而立,每个人与他人和社会必定要发生各种社会连带关系,社会的基础便是社会全体成员由于需要相同和劳动分工而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连带关系)。由于社会连带关系的存在,而有一种基于社会连带关系的社会准则,这些准则构成社会客观法,是国家与法律的基础,个人必须服从,因此权利自然要受到限制。我国现行宪法采用隐含性法律限制方式的条文有许多,例如: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第五,反向式法律限制。依照国外通行之立法例,对公民基本权利之限制,主要指公权力机关应如何秉持社会公益原则,而对公民权利加以限制。从立法例之常规来说,罕有在一个条款中既肯定公民具体基本权利的同时,又规定公民行使该项权利的目的、动机和方式。因为其一,这样立法使人难以辨别立法者的真实动机意在肯定公民权利抑或是否定公民基本权利;其二,成文宪法国家大多要通过部门法将宪法之规定具体化,部门法可更从容和充分地规定公民权利行使的边界,故宪法之规定未免显得多余;其三,纵使由于立法不能做到“无缝隙化”而导致宪法必须“司法适用”,亦可仰赖“司法者的理性”援引宪法第51条和第33条而实现防止“权利滥用”的目标。我国宪法第35条在规定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又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这一规定直接针对个人设置义务,未免混淆了宪法与部门法的不同功能。又比如,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里姑且不论公民人格尊严受到损害的表现形式是否仅限于侮辱、诽谤和陷害,其实暴露公民隐私、暴力残害身体等亦可损害公民人格尊严,因此,本条款无疑存在逻辑不周延的问题,而且,本条款赋予国家一种积极的义务来排除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侵犯,更会造成宪政逻辑的困境。(注2)
二、国外有关基本权利限制的原则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