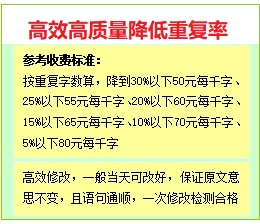(一)苦难与救赎的主题
余华小说在九十年代发生了明显的转向,但小说的主题却有很大的延续性,他依然延续了八十年代小说“苦难”的主题,此时的苦难已不是八十年代那样奇险怪戾。在《在细雨中呼喊》这部过渡性的长篇小说中,作者的笔调开始趋向缓和。余华通过“我”传达一位少年的孤寂与恐惧,但小说深处却有一种呼喊,一种灵魂受难者对温情的极度渴求,尽管这一渴求依然通过人性恶的主题反衬显露出来,但这些都溶化在小说的诚实朴素的叙述之中。人物对自身命运的无知,因而无条件的接受状态使得这部作品较之以往的写作多了许多阴柔悲怜之美。
在以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余华更大的向写实之路迈进,他让我们领略到了那种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作品中温暖和明亮的色调冲淡了阴森恐怖的气氛。一幅仍然充满苦难却蕴含了生之坚韧和生之乐观的图景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这些作品中,苦难依然是小说的主题,任何读过作品的读者都会发现,死亡仍一个个接踵而至,在福贵、许三观身上苦难有过之而无不及,并带有了深沉的悲剧性,但不同的是余华对待苦难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由以前的直接面对转为把苦难当作背景,寻求一种苦难的救赎方式。《活着》中老福贵在他一生中无数次非人遭遇和不幸命运面前的顽强活着,以决不屈服的乐观品格、生命质感和意志强力对抗苦难,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 “人的生命的唯一要求就是活着” (注8),“活着”这种原始的生命强力成为福贵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超越苦难的生存方式。而“这种救赎在形式上是对苦难的超越,在精神上则是对绝望的超越。” (注9)可以说,在余华的小说中,《活着》既是一部最令人沉重的小说,同时又是一部最令人欣慰的小说,贯穿余华以前所有小说的那种浓得化不开的黑色天幕终于在此被撕开了一个豁口,生命的强光由此照了进来。
余华在这些作品中,显示了现实主义因素的增长。现实主义应该具备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一是指一种创作方法,创作原则,更深的一个层面应该指一种精神,关注现实,追问人生存在的终极意义和目的。余华九十年代小说的转变正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吸收,并因此影响到小说的语言等形式方面。
(二)小说形式的探索
这一时期小说虽然发生了转变,但依然具有先锋性质,比如依然使用了以循环叙事为重点的结构,如《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活着》中死亡事件的重复完成了小说的叙事。《活着》中总共出现了七个人的连续死亡。先是父亲因福贵“不争气,’(赌博败了家)而气死:再是福贵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母亲病死;儿子因为抢救县长的老婆被抽血抽死了;后来老婆也病死了;女儿先是不幸哑巴,再就是难产死了;女婿工地上出事也死了;最后只剩下唯一的亲人外孙,也因贪吃豆子而被噎死。但是,由于余华在小说中引入了一个旁观者一一叙述者“我”,从而“与福贵在一起的现在进行时场景频繁地安插于福贵过去进行时的叙述中。时空的转换延阻了福贵的丧亲在叙事上的连续性,重复的死亡事件所积累的悲剧气氛在多次的时空交错中得以淡化.” 因此,叙述重复缓解了或者说冲淡了重复所带来的沉重。这就是余华对命运的理解,对生存哲学的诠释。《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一共卖了九次血,通过对卖血这一事件的重复,余华将许三观为解除生存困境的挣扎活生生地表现了出来,总体来看,《许三观》在重复手法使用上明显要比《活着》复杂和高明许多。比如许三观对儿子的起名问题上,许一乐、许二乐、许三乐,以及小说中还涉及了对其他人物卖血情节的重复。
如果以上是对前期的继承,九十年代小说其先锋性的形式创新性则体现在具有个人风格的对白处理上,典型的如《许三观卖血记》中,他对人物的对话和语言做了最大限度的实验。余华以前那种细密精致的叙述变得放松疏阔,对话的比例特别大。对话不仅是塑造人物的手段,还承担着推动情节发展,介绍社会情况,交待人物经历等各种功能。如果说形式的探索体现了余华的先锋特质,那么探索的方向则体现出对现实主义创作方式的吸纳。小说中,独特的对话方式还成了推动叙事的一个动力,由于第三人称及人物对白的使用和突出,从而使得叙述主体不再像余华80年代小说中只是一个道具,相反,叙述主体消失在人物的背后,人物成了小说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随着人物的一言一行推动着情节的不断发展。由此也说明了“对白叙事”在此篇小说中的重要性和独特性。
向现实主义的回归在形式上还体现在叙述人立场的转变,由精英叙事向民间叙事转化,叙事人的隐退由暴露叙事向隐藏叙事转变。余华曾说: “叙述上的训练有素,可以让作家水到渠成般地写作,然而同时也常常掩盖了一个致命的困境。当作家拥有了能够信赖的表达方式,知道如何应付写作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时,信赖会使作家越来越熟练,熟练则会把作家造就成一个职业写作者,已不再是艺术的创造者了。这样的写作会使作家丧失理想,所以当作家越来越得心应手的时候,他也开始遭受来自叙述的欺压了。” (注10)余华前期小说中充满了残忍的意向和细节,令人毛骨悚然,尤其是叙述着的态度令人震惊,往往以极平静极有耐心的语调对残忍的意向工笔细描,甚至将残忍的意向置于一些温暖柔情的联想描写中描述,整个叙述时时可感知到叙述人的存在。余华一味沉迷于叙述的形式翻新,却渐渐使读者产生了阅读上的困难和审美疲劳。于是后期小说中余华有意避免了叙述者的强烈自我表现,而把叙述人推倒幕后,让人物在前台演出,使叙述更加接近对象本身,达到更深意义的真实。例如《活着》中的福贵,这是一位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他的大部分生命都是以农民的身份完成的。小说中既然选择了这样一个人物来讲述自己,小说就不能再像以前的那种用充满诗情的语言来写,只能用最朴素的语言,必须时刻将叙述限制起来,所有的语调和句式都得符合主人公的身份,在一些意象的描写上,更放弃那种迷离华贵的描述,而只能选择一些确定的、朴素的、作为一个农民能够掌握的语词。
随之而出现的是语言风格方面的变化。先锋是以语言的变化而取胜的,前期余华小说的语言汪洋恣肆,而且大多是模糊不确定的语言。但从《活着》开始余华明显转向确定的语言的运用。确定性语言的美感在于她的朴素与单纯。《活着》没有让人看不明白的句子,不存在理解的障碍和感觉的迷津。《许三观卖血记》中使用的更是单纯而又天真的语言,比如许三观与爷爷的对话:“我儿,你的脸在哪里?”许三观说:“爷爷,我不是你儿,我是你孙子,我的脸在这里。”“我儿,你的身子骨结实吗?”“结实”许三观说:“爷爷,我不是你儿……”对话天真睿智,用轻松单纯的语言写大事(卖血),自有一种不可企及的力量。说中的语言有老人的善良,温柔和智慧,有顽童声调的天真,直露,任性,甚至带有恶意,但全然没有前期小说亦真亦幻,让人捉摸不透。余华放弃语言的恣肆与迷宫,正是让人们真切感受生活的苦难和现实的最本质。
(三)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余华开始用悲悯的眼光看待世界,当他以这种沉静的心态观察这个世界时,发现生活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丰富的多,他开始意识到理解世界而非一味解构世界才是作家应该做的。他开始还原生活,探求生活的真谛。还原生活离不开人物,向人们展示高尚更离不开人物,余华的笔触开始转向人物,开始了对人物心灵世界的描摹,把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深处,通过人物向人们展示高尚,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
正是基于此,余华创作出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这些作品中,“人”被恢复了真实的面目,符号化的人被重新贯注了生命的血肉,“人”也回复了人之为人的本性。在中国九十年代文学人物形象中,福贵和许三观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将坚韧的生命意识和达观、宽容的生活态度传达给了读者。福贵的典型意义在于“活着”。这是一位一生于苦难相随的老人,年轻是因为吃喝嫖赌,胡作非为,而输完了自己的家产,也起死了自己的父亲,被迫以劳动为 论余华小说的创作特征(三)由免费论文网(www.jaoyuw.com)会员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