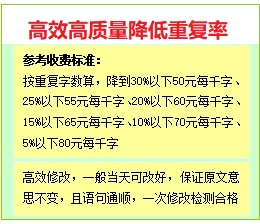总之,中国文人是一个需要救赎特殊阶层。这是灵魂的救赎,因而这种救赎从一开始就永远定格在了渺茫的梦幻世界里。浸淫在科考中的蒲松龄,难以自拔。不过,与绝大多数书生不同,对于科举他有着更多的警醒,亦不乏自赎的意识。在现实的世界里找不到寄托精神、自疗心灵的庙宇,蒲氏用文学搭建了一个。因为这里有年轻漂亮、无所不能的狐女鬼女,这里有起死回生、法力无边的仙人僧人,能把书生们带出苦难的深渊。
三、人性烛照与文人的梦幻救赎
文学的审美境界,在于欣赏作品,从中获得更高层次的生命意义。我们在“聊斋”中感受着厚重的历史内涵,同时产生了悲剧性的崇高感。
一方面是万马齐喑、寒透彻骨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功名心切,却又渺望至绝。在令人癫狂的环境中,蒲氏的花娇狐魅温暖过多少土子冰冷的心。所以,异类更富温情,也更具人性。这些异类有超自然的能量,也有超常规的热量,投向寒士,使之有美可享,有光可循。
蓄积蒲松龄巨大创作的激情,一定是他所处的人鬼颠倒的时代。异族入主中原,对汉族知识分子从意识到言论的禁锢钳制,让人思想窒息欲狂。“文字狱”大面积兴起,手段残忍,令人颤抖。作为一名社会底层的平民知识分子,蒲松龄良知才情奔突,郁积在胸的压抑情绪必须宣泄。从现实的风险中,他反复权衡,选择了一种近乎荒谬的形象塑造手法,营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文学异度世界,“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古典形式中蕴含着现代乃至“后现代”的思想。【注8】
与前人的同类作品比,《聊斋志异》是一部“准举人”又称“挨贡”写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国传统文人写的梦幻小说。
《聊斋志异》以描绘狐鬼见长。在这部小说里,蒲氏塑造了大量自由奔放、光彩照人的狐鬼形象,特别是青年女性形象。她们强烈地反衬出了文人的人格缺陷。
对于文人的人格缺陷,蒲松龄是十分清楚的。他在《张鸿渐》篇中借张妻方氏的话说道:“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胜而不可以共败,胜则人人贪天功,一败则纷然瓦解,不能成聚……”她力劝丈夫在这些人面前不要做出头鸟。可见,蒲松龄批判的目光投向文人的“精英”——在科举场上的蟾宫折桂者,他的笔墨依然十分的犀利。《放蝶》中进士某审案时,按律之轻重,惩令纳蝶自赎,堂上千百齐放,如风飘碎棉,王某乃拍案大笑。严肃的政事被他变成了儿戏。《韩放》中写发生在康熙年间的实事。时值七县水灾,百官不去救荒拯溺,解民倒悬,反而巧立名目,盘剥灾民。科场出生的利津县令用板子敲笞老百姓,用绳子把平民捆来让他们缴输正税之外的“乐输”(自愿多缴的税)。
从受害者到施害者,这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士子由科举完成蜕变的“副产品”。其触目的事实,仍然未能引来文人应有的自省。冷眼旁观,对于同类发迹后的沦丧堕落,蒲松龄已在文学作品中大胆渲泄着这种痛心疾首。
文人需要救赎。可是,蒲松龄找不到现实的可能。由美丽可人的狐鬼美女为主所构建的文学异度空间,是蒲氏苦心经营的另一世界。在这里,他引领读者却看见了明亮的希望。
一步入这片奇异的世界,我们的眼界顿时豁然开朗。各类花妖狐魅纷至沓来。花:花中之王牡丹有《香玉》、《葛巾》,花中君子菊花有《黄英》,花中高士荷花有《荷花三娘子》。鸟:娇婉善言的鹦鹉有《阿英》,翱翔于汉水的乌鸦的有《竹青》。兽:勤劳的田鼠有《阿纤》,狰狞的恶狼有《黎氏》,香气满身的獐有《花姑子》。至于飞翔花间的蜜蜂有《莲花公主》,纤巧的绿蜂有《绿衣女》,《素秋》中的蠹鱼,《白秋练》里的白骥,《西湖主》里的猪婆龙,《八大王》里的老鳖,《青蛙神》里成精的青蛙……天上飞的,地上长的,山中跑的,水里游的,无奇不有。
当然,最多的还是那些可爱的狐女。医术高明的娇娜,追求完美的阿绣,忠贞不渝的鸦头,爱花爱笑的婴宁,聪明机智的小翠,娇羞无邪的青凤……她们从天上,从山中,从水里,从大自然的各个角落向人走来,献出一片赤诚,一腔热爱。
范十一娘因父母嫌贫爱富,不能同心上人孟生结合。她的女友、狐女封三娘不顾瓜田李下之嫌,深夜造访孟生做曹丘生。范家父母将女儿许贵家,十一娘自尽,封三娘用不死药救活,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小翠向王家人报恩,帮王家人治好了傻儿子,并在官场获胜。娇娜用自己的仙丹为孔雪笠疗病;凤仙在镜中监督夫婿上京读书;辛十四娘帮冯生解脱冤狱;舜华在张鸿渐困窘时给他无微不至的爱护……狐女鬼女助人的故事像一支支温柔的小夜曲,抚慰着走在歧途中的读书人残缺的心灵和破裂的伤口。
如果说《聊斋志异》中花狐鬼魅读书人的知音和拯救者,那么穿插其中的狐叟便是智慧的化身或人间长老的再现。《聊斋志异》中的狐叟极具风采,他们依然保持着和读书人的亲密接触。《九山王》中狐叟以千金向李某借的荒园,阖家搬进,荒园从此酒鼎沸于厨中,茶烟袅于廊下,一派恬静。园主李某却残忍地将狐叟一家放火烧死。幸存的狐叟化身为南山翁说服李某^造**,终于让李某遭灭族之灾。“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聪明的狐叟运筹帷幄,智若孔明。《狐嫁女》中的狐叟慧眼识得少年贫穷的殷士谵为“殷尚书”,将这婚礼的不速之客尊若贵宾,出妻献子,酒肉款待,殷偷偷将狐叟金爵纳入袖中,狐叟明知,却“急戒勿语”,雅量非凡。《凤仙》中的狐叟则与人间相同,嫌贫爱富,对衣袍炫美的女婿,以金盘进田螺婆,对衣衫褴褛的女婿,不理不睬。
《聊斋志异》中的妖媪常是贤妻良母。这里面有花姑子热情待客的母亲,青凤温文尔雅的婶母。《巧娘》和《狐梦》中风韵犹存的狐媪们为女儿做媒。而最具意味的当算是《白秋练》里的白媪。白秋练爱上了风流儒商商慕生,相思病苦,她的母亲便出面向慕生自媒。慕生因为父命缘故婉拒,白媪便施展法术阻止商船北渡,造成慕生与秋练幽会的机会。在女儿的爱情生活中,白媪成了送简抱被的红娘。龙君闻秋练美色,欲纳为妃,白媪坚拒不从,被流放几死。这位白骥幻化的老媪开明且慈祥,是女儿爱情的护法神。
在蒲松龄的世界里,文人不可没有妖狐帮助,妖狐却难得有几回求助于人。妖狐们手中掌握着金灿灿的大门钥匙,走进那道门,文人们就是幸福的了。狐妖是文人们、特别是落魄文人们的救世主。
人和妖在矛盾中寻求着和谐,她们的形象在矛盾中显得越发可爱,亮丽。而与此相对应,文人们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了。文人的人格无法与狐妖抗衡,背信弃义者总是那些道貌岸然、峨冠博带者。在这里蒲松龄的笔墨十分尖刻,甚至剥下了文人们最后的伪装——所谓的才学。
当然,蒲松龄的骂并不仅仅停留在泄泻“胸中块垒”,他其实有更深层的意义和更美好的愿望。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认为,聊斋非独文笔之佳独有千古,更重要的是议论醇正,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乃有益身心、有关世教之书。唐梦赉的序文也说,蒲松龄的书总是从赏善罚淫的主旨出发,从有益于教化出发,一片救世婆心。
人鬼观照,道德立分。不难看出,蒲松龄在异度空间塑造花狐鬼魅的真正目的,乃是为了让那些沉沦在苦难之中的文人们从性格、品行、人格上得到更大的完善。
四、终极关怀:虚幻中的真情
超越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聊斋》着意于对人生本质和意义的探询,这使其的文学审美价值达到了终极关怀的巅峰。
我们不必怀疑社会对人的异化作用,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自己的立世态度。社会的异化,扭曲了人的灵魂。在黑暗肮脏的社会环境中,蒲氏笔下的异类却生出浓厚的人情,温暖着人们冰冷的心,弥合着破碎的灵魂。
“美妇、富有、修龄(长寿)、香火连绵和一生平安,这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存在的理想和愿望”。【注9】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连读着书、有思想的文人都觉得它是南柯一梦,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了。不过,这些在《聊斋志异》中我们得到了“实现”。
在《陆判》篇中,朱尔旦对美妇的渴望,得到了满足,虽然其遭遇匪夷所思,但相比于聊斋里众多的有过艳遇的穷书生们又算得了什么呢?人间世俗的美女嫌贫爱富,又怎么和心地善良、性格独立的狐妖美女们相比呢?那才是一种发自内在的美。
财富,也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向往和追求。但读书人除了金榜题名才能做官发财外,别无它途。金榜题名几个人?其他人就只好甘受一辈子的贫穷了。聊斋为这些贫穷的读书人带来了希望。
在《辛十四娘》篇中,辛十四娘离去后,广平冯生以禄儿为室。逾年生一子。然比岁不登,家益落,夫妻无计,对影长愁。忽忆堂陬扑满,常见十四娘投钱于中,不知尚在否。走近一看,则豉具盐盎,罗列殆满。逐件移去,箸探其中,坚不可入;扑出碎之,金钱溢出,由此顿大充裕。 探析《聊斋志异》中花妖狐魅形象的艺术特色(三)由免费论文网(www.jaoyuw.com)会员上传。